
那丑
LV1 2016-08-18【微澜之下】
作者:那丑
连载最近更新: 第七天二零一二年七月十八日 星期三 阴 嘎噔噔,嘎噔噔,嘎噔噔,嘎噔噔……从潭城到农村老家,坐火车只要四五个小时,可我母亲给我买了张卧铺票。她非说我累了。现在她也在火车上,半个小时以后到潭城,去处理我留下的事情:寻找失踪的,照顾犯病的。中间的空档,我请了亮河帮我盯一阵儿。我母亲坚决不许我在老人家里...
作品简介:一个高中生住在高龄的伯祖父母家里,在这期间,他认识了隔壁的画家和他的女儿。在和这两家人看似普通的交往之中,青春的暗流涌动,亲情、爱情、性和审美的启蒙在悄无声息中完成。作品为日记体,并尝试用一种准表现主义的、记录梦境的方式来书写平静生活之下复杂的心理活动,主人公的期望、欲望、恐惧和焦虑,并展示作为一个历史的他。
5562 票-

那丑
楼主 LV1 2016-08-18第三天二零一二年七月十四日 星期六 晴转阴 今天上午,我见着亮河的女儿了,她叫朱鹤,我叫她鹤姐。她比我大十岁,在艺术博物馆工作,也在那儿住,只有周末回来待两天。她好像很喜欢我,一边把包摘下来挂到墙上,一边就对我问长问短的。我画画的时候,她在我后面的沙发上坐着看我。我虽然看不见她,可这仍然让我很紧张,觉得一团火在我身后烧着。我知道自己很笨,连怎么拿笔都不太清楚,但她也没笑话我,反而是在我自己想到了一些办法来解决难题的时候,她笑出了声。亮河并不从线条之类的基础开始教我,他让我自己先画,然后一点一点地来帮我修正错误的画法。他说,这样才能让我明白为什么要那样改。今天我画的是他家的暖壶。那是个红色的铁皮暖壶,现在很少有人用了。一边画,我一边听鹤姐和亮河讨论下星期一个印象派画展的事。他们两人说话的声音都很好听,又亲切又随便,不像父女,倒像朋友,谁也没打算去教导或者说服另外一个人。我想这就是成年的好处吧。但这也不光是因为她成年了,还因为他们都懂画,有共同语言。鹤姐留我吃午饭,我推辞了半天,最后还是答应了。我给伯祖母打了个电话,告诉她我中午不回去。鹤姐炒了三个菜,其中有我最喜欢的西红柿炒鸡蛋。她的做法和我母亲的不一样,她把西红柿切得非常碎,让汁液和鸡蛋混在一起,尝起来酸酸甜甜的,一点都不腻。鹤姐问我家里的情况,我开始没提我父亲,她可能觉得我不方便说,就没再问下去。我觉得她真体贴。不过后来,我还是忍不住说了父亲的事:他在我十岁那年离开了我。别人都告诉我说,他在外地抓逃犯的时候殉职了,是个英雄。母亲对我一直很严厉,父亲去世后,她就不光是严厉,而且经常无缘无故冲我发火,好像是我把他害死了似的。我说了这些,鹤姐流泪了,可她马上就擦掉眼泪,笑着给我夹菜。亮河在旁边低着头,我想他一定也替我难过吧,只是没有表现出来。其实我自己早就好了,不需要别人安慰我。我后悔了。离开餐桌的时候,我说我去洗碗吧,鹤姐不许,让我到沙发上躺着去,下午好继续上课。正在这时,亮河接了个电话,我听见好像是说,有个领导要参观学校的展览室,让他下午去接待一下。他和电话那边的人说话非常客气,甚至有些卑躬屈膝的意思。我突然有点可怜他。他放下电话,就回屋换了一身新衣服,白衬衫和他发暗的脸色显得不太搭。他安顿鹤姐,让她下午给我上课。临走的时候,他用手在我右肩膀上轻轻地扶了一下,他的手心烫乎乎的。我按照鹤姐说的,在沙发上躺下,但我睡不着。听到厨房不再叮当乱响,鹤姐大概是回卧室了,我就再也闭不上眼睛了。屋里很热,我轻轻地下地去开了一扇窗子,然后就坐在沙发上犯愣。我想上厕所,可我不敢去,因为我必须路过鹤姐卧室的门口,我怕她误会。我只好坐着,像昨天一样看那些画。看着看着,我就睡着了。我还做了一个梦,但是因为睡得并不舒服,梦也不是美梦。后来我听到一声门响。不是外面的门,是鹤姐从卧室里出来了。我才知道,她一直是关着门的。鹤姐换了一身橘色的半袖、短裤,头发跟亮河一样也扎成马尾。她很苗条,比油画上那些胖乎乎的模特们好看多了。我们就在下午的阳光里开始上课。她坐在我旁边,非常细心地给我示范,给我讲软硬不同的铅笔和炭笔分别都什么时候用、怎么用,还把自己新买的一套炭笔送给了我。现在它们就被我藏在书包的内袋里,我决定将来能画肖像的时候再使用这套炭笔,而且只在为她画像的时候才用它们。下午五点多,亮河才回来,他看起来非常累,直到回卧室换上了一身旧衣服,他才张口说话。不过他没有抱怨,只是问我下午学得怎么样。鹤姐说我学得很快,还把我画的第二只暖壶给他看。亮河点点头,说我的那些毛病看来并不深,一个下午基本上就都扳过来了。他的评价听起来没有赞美的词,可是比鹤姐的夸奖还要让我脸红。我没有留下吃晚饭。回家见到伯祖母,她的脸色有点不对劲,没有生气,可也不像昨天那样热情,说话时眼皮耷拉着。我不确定是什么原因,也不敢问。伯祖散步回来了,他一回来就开始扫地,扫完地又拖地,然后再扫地。伯祖母也没有向平常那样拦着他,只由好我去很费劲地告诉他,他刚才扫过一遍了。这时,我闻见一股很刺鼻的气味。一抬头,我吓了一跳,原来阳台上的几盆花从头到脚都被烧焦了,黑乎乎的一大片,残破的叶子和花瓣掉得满地都是。我连忙去扫,一边还问伯祖母这是怎么回事,她便指着在沙发上看报的伯祖,咬着牙说:“还能有谁!你大爷爷干的好事呗。现在你去问他,他肯定告诉你他什么都不知道。”我也没有去问。我觉得就算是伯祖烧的,那么大岁数头脑不清楚的老人,谁能责怪他什么呢?他可能是把花草当成过年笼的旺火了。我听说年纪越大,就越容易想起小时候的事儿。伯祖母发完火,心情就好多了。她还主动去帮着伯祖把运动鞋脱掉,给他端来晚饭,然后安顿他上床睡觉。这是挺温馨的一幕。两人毕竟是老伴,相依为命这么多年了,谁也不会为了这么点过错就不肯原谅对方。他们这样的感情也值得我们这些年轻人好好学习。不多写了,我要睡觉了。明天早上我去亮河家,又能看见鹤姐了。我真希望他们就是我的父亲和亲姐姐! 第三夜前半夜的梦:我在河岸上站着。我想下去。我怕它凉,我怕它把我带到一个不熟悉地地方去。河边的花丛里,花瓣变了颜色。黑斑蜕掉了,露出鲜亮的橙色来,在暖和的微风里摇摇荡荡的,像火一样烧着。我看它们实在可爱。我弯下脖子,衔了一束在嘴里。花的红色,花的火焰,顺着我的血管流动,在我的羽毛上燃起。我不再是一只鹅了。我站了起来,看见自己在水面上的倒影,凹凸不平、簌簌乱抖的,可我认出来了:我变成了一只火烈鸟。长长的腿脚,鲜艳的羽毛,我走进冰凉的水里,水也变成温热的了。我嘴里的花,它的颜色都流到了我身上,它慢慢地变成一种纯洁的白,就是鸽子的羽毛那种白,天边的白云那种白,婚礼上的鲜花那种白。我四处踱步,浑身冒着自信的光彩。我来到死水边。突然,我看见岸上躺着一具尸体。一只鸽子,本来是白色的,现在变成了漆黑,有黑色顺着它的血管、它的羽管渗透到它全身。是什么杀了它?我没有亲眼看见。我担心那是水里的东西。 后半夜的梦:亮河开着车,我坐在后面。没有别人。我跟他说话,他不理我。他哼着歌,跑着调,可我知道,这是他最喜欢的那首《少年壮志不言愁》。他不会唱别的。他的声音听起来那么奇怪,好像是电话里的声音、广播里的声音,或者梦里的声音,和我隔着一层。窗外黑漆漆的,只有忽明忽暗的路灯。车正走在大桥上。我知道,我们俩不在一个地方。也许他不在这儿,也许我不在这儿。我都知道。可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,或者车轱辘底下发生了什么。他猛地一转方向盘,脚底下踩的不知是刹车还是油门。车头撞断了栏杆,一点儿声音也没有。车子从桥上飞了下去,一点儿声音也没有。它掉进了江里,可我没有。我还在桥上站着。我什么都没听见,只听见他的嘴里还哼着那首跑调的歌。奇怪。我很悲伤,可我不惊讶。我好像来过这儿不止一次了。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去的。一睁眼,我躺在床上,身上空落落的,什么都没穿,盖着被子。周围的家具都是橙色的,暖暖和和,又好像藏着什么危险。我的身体很舒服,但我心里没有底。我不该躺在这儿。一扭头,我旁边躺着个女人。那是鹤姐,扎着马尾辫,醒着,没穿衣服,也没盖被子。她侧躺着看着我,发现我也扭过头来,就笑了。“怎么,不喜欢我?”她说。我浑身冒冷汗。我在哆嗦。因为我尿炕了,就在她面前,不过隔着一层被子。可她还要伸手去掀我的被子。我用两腿夹住,死活不让她掀。可她力气比我大,最后还是掀开了。可我没有尿炕。那不是尿。她没有嘲笑我,但她还是笑了。我听得出来,是温柔的笑,体贴的笑。我流泪了,但我没有哭。我安心了,因为现在谁也伤害不了我。她可没碰我,只是和我对视着。她好像在等谁。果然,他来了。亮河推开门,一股凉风吹了进来。这时候,我开始有点怕。可他来到我旁边,手按住我的肩膀。他的手真暖和!他不是鬼。他复活了。“如果你还不理解我们,我可没办法了。”亮河笑着说,可是他没有看我,也没看他女儿,而是看着对面墙上那幅画,“女儿,你回去吧。”鹤姐从床上起来,把束发的皮筋褪到长发的中间,脚步轻快地走向画框。她慢慢地融进画里,她的皮肤变得像鸡蛋壳一样光滑、坚硬,而且有细微的裂痕。她站到了贝壳上,周围是玻璃一样易碎的水面。她又变得忧郁起来。“她不是忧郁!”亮河说,“她那是对凡人的世界不习惯!不习惯有一个身体!可是要没了身体,谁又能认识她呢?你想想,她可是美神哪!神像和鲜活的漂亮姑娘,区别在哪儿呢?……”慢着。这句话我听着耳熟。这时候,我觉得我理解他了。我看着那幅画,觉得他的手热乎乎地在我后背上搁着,我真想哭出来,因为我感觉到了幸福。这时候,就有一种声音开始喊叫。不知道那是女人,还是男人,还是别的东西。从地底下传来的。像开了锅一样,那声音伴随着热气。不是水汽,是干燥的空气,还有焦味。我害怕地想钻到亮河怀里,可他突然不见了。 -

那丑
楼主 LV1 2016-08-18第四天二零一二年七月十五日 星期日 阴 今天早晨,伯祖母躺在床上起不来,说是胸口不太舒服。我吓坏了,因为我完全不知道犯了心脏病该怎么救,连忙救去找手机打120。伯祖母说不用,她只要在床上安静地躺几天就好了,让我把救心丸找出来,放在床头预备着。她的眉头都拧到了一起,每说一句话就得喘几口气,我就让她尽量不要说话,躺着别动。我给她倒来了温水,插上一支吸管,放到嘴边。她喝了几口,眉头算是展开了,还没来得及说话,可看着我的眼神非常奇怪:那么明亮,那么专注,简直不像一个老人的目光。她好了一点之后,我赶忙上网查心脏病的知识。看来让她少说话、少活动是对的,而且救心丸放在舌头下面,比直接咽下去更有效果。我就把这些念给她听。她盯着我,小声说,我该去学画了。我笑了笑说,今天我不去,她身边必须一直陪着人。伯祖母的嘴角开始一抖一抖的,我有点紧张,以为是她又犯了病,可马上我就发现,那是她想笑而又笑不出来的表现。我跟这位瘦弱的老人对视着,突然之间,我的笑容不那么尴尬了,而且我感觉,以后也再不会尴尬了。半个小时之后,伯祖母好多了。我扶她靠在床头上,在她的腰底下塞了两个枕头。她已经可以轻声说话、伸手拿杯子了。这时,我听见一阵门铃响,就去开门。鹤姐站在门外,穿着她昨天从外面回来时穿的那身短袖运动衣。她问我怎么没去上课,我就把伯祖母犯病的事告诉了她。她跟我一起来到老人的床前。我们俩差不多是一块儿进的门,伯祖母盯着我们,显得特别惊讶。我一提醒,老人才认出她是谁,可我马上就后悔这样做了,因为老人的脸上突然露出一种表情,这种表情我之前好像见过一次。“哦,闺女。你和你爸一起住啊?”她的口气听起来也酸溜溜的。“嗯。”鹤姐很快地说,“您好点了吗?”“哎,每次犯病都得躺个一两天的。现在还行,一会儿就说不准了。现在是你爸教他画画呀?”“这两天我爸学校有事儿,是我教他。”“噢……哎呀,他今天可能去不了。要不你就在这儿教,你让他看着我,我也顺带看看你们怎么上课呢。”“……其实也不着急这一两天。让燕明再消化消化昨天的课,自己练一练吧。”鹤姐不太自然地笑着说。“行,那就这样吧。你也歇一天,不麻烦你了,你是放假回来的吧?”“嗯。”鹤姐点点头,可她不想再和伯祖母说话了。她扭过头来,眼神忧郁地对我说:“明天是星期一,我晚上就得坐城铁回单位。下星期学校放假,我爸能腾出时间来教你了。不用我留下帮忙吗?”说后半句时,她朝伯祖母那边扬了一下头。我摇摇头。虽然我很想让她留下来,可如果这样,她肯定也不会自在的。而且我心里没底,不知道老人为什么不喜欢她。只是因为那种去不掉的偏见吗?如果是别的原因,我害怕老人憋在心里,对身体更不好。就这样,鹤姐走了。我希望下个周末还能见到她。可她还愿意见我吗?我心里很难受,可是不敢表现出来,因为伯祖母需要安慰,而不是刺激。对老人,我们就应该宽容一些,尤其是对我们的亲人,而且是深深地依赖着我们的亲人。老人家灰白的头发间脆弱无助的眼神,难道还不能唤起一个人的责任心吗?等伯祖母能从床上坐起来了,我就搀着她到客厅去,陪她看了两个小时的电视,等伯祖散步回来了,我就去做饭。我本来会做很多菜,可今天想也没想就做了西红柿炒鸡蛋。我学着鹤姐那样,把西红柿的汁液溶进鸡蛋里,而且没有放葱花,让一盘菜里没有一点黑色,全都是火辣辣的鲜红和亮黄。一边铲炒,我就一边流泪,想象着鹤姐如果在旁边看到我这样做菜,她会不会原谅我。盛盘的时候,我把鸡蛋铲成小碎块,让伯祖、伯祖母吃起来方便一些。主食我熬了米粥,但我忘了粥需要好长时间才能熟,后来我又把鸡蛋热了热,才端到他们面前。我本来担心伯祖会给帮倒忙,让伯祖母的病再犯一次,可她冲他指了指自己胸口,他就像个懂事的孩子一样躲到角落里去看报,不再麻烦她了。我把粥锅端上茶几时正好看见了这一幕,脸上被蒸得热乎乎,心里也被感动得热乎乎的。伯祖看来已经习惯我了,虽然他还不知道我是谁。看报时他还指着一个字问我这念什么,我过去一看,鼻子当时就酸了:每天一定要读几小时报纸的他,已经糊涂到连“大会”的“会”字都不认识了。习惯真是一种可怕的力量,它强大得,怎么说呢,就像一颗包裹得严严实实的蚕茧,就算里面的蚕已经死了,茧却还在那儿,还是那么结实。两位老人都没有午睡的习惯。伯祖一边手里捧着报纸,一边每隔十几分钟靠在沙发上打个盹,一两分钟后又准醒,继续看报。伯祖母则一直很专心地在看书,是一本哲学书。我在旁边写一会儿作业,画一会儿素描。就这样,一个中午过去了。下午三点左右,伯祖母放下书,摘下眼镜,好像很累、或者很失落地叹了口气。她让我把她书柜里的那个手提箱搬出来。搬来之后,她又让我从侧兜里找一本硬皮的证件。我伸手掏了半天,找到一个有小孩的手那么大的红色布面小本,上面印了三个繁体金字:“记者证”。我打开一看,第一页的右边就是伯祖母三十多岁时候的黑白照片,左边写着她的名字——吴涟、发证单位——潭城日报社,和发证时间——1959年X月X日。哦,原来她以前当过记者。她从我手里接过小红本,仔细地翻来覆去,看了又看,用枯瘦的手指在照片上那张年轻的脸上摩擦着,脸上带着自豪的微笑。她告诉我说,当年的很多地方大事、甚至国家大事都是她跟踪报道的,她也报道过许多劳模的先进事迹,自己也被很多次评为省劳模、全国劳模,八十年代她退休了,还有记者来采访过她,她的事迹也登上过各种各样的报纸。她让我打开箱子,我看见里面搁着一摞报纸,比三本新华字典都厚,她说,这些报纸每一份上都有她的文章。听到这些,我惊讶得快要说不出话来了。她让我从里面随便挑她的一些报导来念。我读了一篇,她还让我读下一篇,再下一篇。我一连读了六篇,她开始是闭上眼睛听,后来听着听着就开始轻轻地笑,但不像是欣慰的笑、反倒像是苦笑。当我念到第七篇的时候,她伸出手来让我打住。她的眼睛闭得紧紧的,好像在逃避眼前的什么东西。“别念了。”她哑着嗓子说,“都装起来,给我扔楼下去。”我还以为她也像伯祖一样糊涂了。可是她随后就说,她当了三十年的记者,却从没有在报纸上写过多少她自己的看法、自己的真心话。她只报道那些“该报道”的东西,但她从来就没有想清楚过,到底什么是该报道的、该让读者知道的。她到处跑新闻的时候,她得在文章里体现主编的意思;等她当了主编,她又要在报纸里体现更高级的领导的意思。除了领导的想法,她还要顺从读者的想法,考虑读者欢迎什么样的立场、反对什么样的态度。这两把尺子仿佛就规定了“真理”这两个字该怎么写。几十年里,她好几次想要写一部小说,可她始终找不到自己说话的风格,甚至不知道“该”写什么。她说她非常明白,文人需要凭着良心来写作,可是“良心”在她这里,已经没有那么鲜活、那么直观了,它变成了一架不容深思的审判机器。她分不清说话和思考,她的头脑完全被词语带着走,她不知道是她的脑子在转、还是那一架机器在转,或者她的脑子就是那一架机器的一部分。她说这些话,我好像理解了一点,可还是不会用我自己的话转述出来。她遇见的困难可能是我这种年龄、我这种层次的人没遇上过、或者永远也遇不上的吧。可我有过一些类似的感觉,我对她说了。人有的时候就觉得自己轻得像一只塑料袋,你不知道你为什么飘来飘去,从来不能像一颗种子一样落进土里、生根发芽,可是你又不得不飘着,因为你还要活着,狠不下心来去死。几年前我爸死的时候,全世界都告诉我他死得特别英勇,让我将来要学他的精神,可我后来听见我妈和我姥姥聊天,才知道那就是场普通的车祸,他开着车从桥上冲进河里去了。当时是下雪天,我不知道是路滑,还是因为他根本就想去死。为什么我这么猜呢?我也不知道。可能是我打心眼里不愿意那是个偶然事故。一场事故杀不死他,他不该死得那么荒唐。可这世界就……[1]这么荒唐。下午出去买菜的时候,我真的把那个手提箱、连同伯祖母半辈子的劳动成果全都扔进了垃圾堆。冒着黑烟的垃圾堆里什么都有,泛着一股烧塑料的味儿。我突然觉得我也在里面被缓缓地烧掉了。晚上,我做了饭,安顿刚散步回来的伯祖睡下,就开始写作业。伯祖母就在我旁边躺着,可我很少和她说话。九点多的时候,她终于睡着了。我回到屋里写日记。还能怎么样呢?这就是我的一天。 第四夜前半夜的梦:我慢慢地在死水旁边踱步。我从水面上看见了自己鲜红的倒影。慢慢地,死水发生了变化,它变得不那么黑、不那么暗。它开始流动。它变成了一条深色的河流。我迟疑不决地迈向它,直到我的腿浸在里面,我甚至能感觉到水流的力量。水悄悄又变回了黑色。刚才死掉的鸽子在扑棱翅膀,活了过来。它刚要飞走,被水里窜出的一条蛇,一条漆黑的、没有眼睛的蛇,一口给咬死了,甚至都没挣扎一下。我知道,我看见了它。我自己浑身像被撕扯地那样疼。剧烈的疼痛。之后,我被撕开了。火烈鸟从我身上猛地一下飞走,飞向天空,那团火灭了,被乌云遮住了。我变回一只鹅,浮在水面上,失魂落魄地悲哀。我还想飞走。那黑蛇从水底游了上来,在我周围盘旋,好像只要我一展开翅膀,就要立刻冲上来咬住我的脚掌。我的脚掌是我天生属于水的部分,它们是我的,可又背叛我。我只能继续游着。水也不再流动了,黑洞洞的,蛇也潜回水里,只在水面上露个脊背。我也累了,不想再飞了。天空中飘下一大片像雪花一样的东西,那是火烈鸟嘴里叼着的白色花瓣,它们落到死水的水面上。它们沉了下去。 后半夜的梦: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,巴黎卢浮宫举办法国印象派油画展,有莫奈、塞尚、波提切利、萨特、福柯、黑格尔、宗白华、朱光潜、鲁迅、邹韬奋等画家的名作,由博物馆研究员朱鹤女士担任讲解员,展览将面向全社会开放,由二十一日到二十八日持续三个月,这一盛事……今天《潭城日报》的头条,是一篇展览会的报道,伯祖母写的。她刚从那儿回来,脖子上挂着照相机,一脸怒气。我问她为什么这样生气,她说博物馆的人拦着不让进去,连一个工作人员都没有采访到。我说,就算这样,她的报道也上了头条,可见她多么受领导和群众的重视。这让她宽了心,她就坐在沙发上开始喝保温杯里的茶。可是她喝完茶就去卫生间干呕,说她恶心,但什么都吐不出来。我怀疑她知道了。我手里有一张门票,鹤姐送给我的。我在兜里把门票攥得很紧,生怕伯祖母抢了去。可我又可怜她找不到新闻素材的那种难受劲。票早就卖光了,鹤姐说,一张都没剩下。她让我一定要去,要不然就再也别想看见她。我正在犹豫要不要把票给了伯祖母,可想着想着,那一天就来了。我迈出门去,打车到卢浮宫,走了很长时间,天都要黑了。哦不,现在还是上午十点。外面那是阴天。我听说今天就是世界末日,黑沉沉的天空,也许是火山灰吧。天气真热,开车的阿姨把衣服全都脱了,我问她是不是要去美院做模特,她说没有,就是热。我也很热。可我不好意思脱衣服。下了车,我发现卢浮宫门前的人很少。大概是因为今天世界末日,没有人来欣赏艺术了。我走了进去,检了票,上了站台,一列火车在我面前停下。列车员告诉我,先上车,后看画展。原来画展在火车上。我走到七号车厢,那是一个大厅,金碧辉煌的,穹顶高得像一座教堂,所有的画全都挂在墙上,而且全都没装裱过。最高那一排,想要看的话得爬上摇摇晃晃的脚手架。有一个人正站在脚手架上,拿着话筒讲解,我爬上去一看,那不是鹤姐。我不认识她。鹤姐没来,虽然门口的海报上写着她的名字。我一边忍不住流泪,一边向她打听鹤姐的去向。她说,鹤姐刚刚下去了。我就朝密密麻麻的人群里看,却什么都没找着。我就跳下去,像鸟一样展开翅膀。我往下坠得太厉害,差点摔在地上,可还是飞起来了。我的眼睛不在原来的地方长着,而是在我的背上。目光越过我的脑袋,和我一起寻找着她。我知道我一定能找到。我的眼睛都快出血了。最后,在一个角落里,我看见一个女人。她很像她,那么,我就努力地把她想象成她。我朝她俯冲过去。我知道,这几秒钟的时间里,如果她还不变成她,我就再也没机会了。最后,我成功了。我就这样找到了她。我控制不住自己。我面对面地去拥抱她,把她整个抱在怀里,我们的胸贴得紧紧的。她喘不上气来,还在我耳边不停地说:“你找到的不是我,你找到的不是我……”我知道她不会说谎。可这是什么意思呢? [1] 此处作者涂掉两个字。 -

那丑
楼主 LV1 2016-08-18第五天二零一二年七月十六日 星期一 阴转小雨 现在已经快十二点了。我很累了。今天发生的一些事,让我非常难受。但我得把它们记下来,不能撒谎。伯祖母早上又犯病了。她说自己难受得比昨天还厉害,所以我还是像昨天那样,让她千万不要动,我帮她洗脸,做早点。整个上午,她不停地用那种虚弱的声音跟我描述这些年她孤独的日子。她说自己报导了那么些个大事件,可是到头来,那些事件没有一个是因为她的报导才被写进历史书的。该被记住的,没有她的努力也被记住了;该被忘记的,也并没有因为她而被记住。现在连她自己都被别人忘得一干二净。我听她说得伤感,就让她继续说下去,她一连说了一个上午。我既担心她话说多了心脏受不了,又觉得让她说说,心里痛快些也好。但不管我怎么想,我肯定是拦不住她的。可是后来,我发现伯祖母在骗我。她根本就没有犯病。中午吃饭的时候,我就觉得她的表现有点奇怪。她总是在重复一句话:“我难受,吃不下了。”虽然我看她的脸色并没有昨天早晨那样惨白。她确实吃得很少,可吃饭的速度并不慢,不太像是没胃口的样子。我扶她上沙发去躺着,然后我去冲了个澡。洗着洗着,我就看见有一道阴影从门和地面的缝隙中一闪而过。我洗澡从来不开灯(因为我一看见浴室贴的白瓷砖就会头晕),所以才看得这么清楚。大约五分钟后,这道阴影又闪了过去。我知道这不可能是伯祖,他早就去睡觉了,而且就算醒着,也不可能走得这么快。出来之后,我特地去厨房看了一眼,只见剩下的饭菜都少了很多。我这才确证了我的怀疑。这时候,我真的开始害怕了。伯祖母为什么要说谎呢?回到客厅,伯祖母还在那儿躺着,说话也是有气无力的,显得比上午还要虚弱。我和她对视了一阵,最后也没说什么。在我看来,她几乎连个撒谎的理由都没有。假装吃不下饭去,这是为了继续装病。可装病又是为了什么呢?要是想让我不再去学画、而是陪在她身边,那么她为什么不直接说呢?这是在她家,她又是我的长辈,她又是个大人物。我可怜她,我理解她。但是我害怕她。我已经不敢相信她说的每一句话了。前天,客厅里的那些花呢?我知道,伯祖只会做他习惯做的事。晚饭后,我很早就回屋了。这间屋子给我的感觉,和第一次看见它时不太大一样。它变得阴冷阴冷的。我在冰凉的地板上走来走去,总觉得墙上那些遗像在盯着我,眼睛随着我的来去而左右转动。后来我实在受不了了,就穿起衣服,偷偷地跑出门去。幸好他们都睡了。我关上伯祖母家的门,去敲亮河家的门。他当然没想到我会这么晚来。我把这几天的经历跟他说了,包括伯祖母骗我的事。亮河露出了他接电话时的那种笑,说老人家肯定有她的难处。我本来想着他会站在我这一边的。真的,他的马尾辫和这种笑容非常地不配套。他请我吃了夜宵,还问我明天来不来上课,我就哭了。因为我想到以后不知该怎么办。我说不想回去,想住在他家里。我知道他不会同意,可那时候忍不住。我甚至想过装病,就像伯祖母那样,可是亮河不会看不出来的。果然,他说不行。他的理由是家小,没地方。他都懒得用别的理由来回绝我,大概是觉得我太幼稚了,听不进道理去。我就说,我可以住在鹤姐的卧室里,等她回来了我在到沙发上去住。没想到刚说出这句话,亮河就生气了。他没有大声喊叫,而是突然铁青个脸,站起来赶我出去。他这两天没刮胡子,挥胳膊的时候十个指头也绷得很直,好像电影里那个剪刀手爱德华。他关上门,我就站在楼道里。声控的灯亮了一会儿就灭了,可我还站着。就算他从猫眼里看着我,后来也看不见了。那时候,谁也看不见我,我自己也是。我累了。我哪儿都不想去了。我真后悔去敲亮河的门。现在,我趴在床上写日记,还是在这间阴冷的屋子里,墙上还是有那么多被压扁了的死人看着我。可是我一点儿都不怕了。人累的时候,真的,什么都挡不住他去找个平整的地方、一觉睡够了再说。写这种睡前日记,除外。 第五夜前半夜的梦:我在水面上浮着,浮了好多天了。我脚上的蹼都给泡得皱了起来。死水就是死水,它又变回以前的样子,而且更浓,更黑,蛇的脊背一会儿浮出水面,一会儿沉下去,到处冒着灰色的气泡。我知道我脚下的那些水草,其实都是蛇,它们从各个地方露出头来,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一齐窜上来把我拉进水底。我的两只眼睛往外突着。有一只鸽子从我身上飞了出去,带走了我的眼睛。我的眼睛长在它背上。它好像是我,可它不是。我的蹼还在水底划着,我的肚子还浮在水面上。鸽子飞向对面那条波光粼粼的大河。它飞得不太稳,摇摇晃晃的,可也没掉下来。它落在水面上。它想要浮上去,可它是只鸽子,它身上没有属于水的部分。它挣扎地落到岸上。它看见开满白花的河岸上,那些白花都长出了斑点,越来越浓、越来越黑、越来越大的斑点。那河流开始变暗,最后停止流动,变成了死水。鸽子想要飞回来。它飞到半路就掉下来了,摔进了淤泥里。我的眼睛也摔进淤泥里。它们闭上了。 后半夜的梦:我去买早点。伯祖母说巷子口那家的羊杂碎还不错。在豆浆馆门口,我碰见我妈了。她刚吃完早点,狠命地擦嘴,然后一边走一边拿个小镜子补口红。她穿一身白,连高跟鞋也是白的。她不是去上课,因为学校放假了。马路对面是个别墅区,门口有一家咖啡馆。我跟在她后面,看见她进去了。墙是玻璃的。她坐进最里面的一张长椅里,不到一秒钟,不知道从哪儿闪出个男人。他穿一身西装,刺眼的白。他走过去,两团白色就凑到一起了。他们在亲嘴。我的两只眼睛突然开始火辣辣地疼,头也疼,我一头就栽到外面长椅的椅背上了。我擦着眼泪,可是越擦越多,眼睛里甚至开始流白浆子。我是不是瞎了?到处都是白的。我勉强能睁开眼睛,看见了一个让人发疯的白世界。我只好再闭上眼,摸着黑走路,透过眼皮还能看见一点路。可我最后还是转圈了。亮河在我面前站着。我盼着他进去咖啡馆瞧一眼,可是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我的嘴就像被白胶水粘住了一样。亮河到底死了没有?是没死,还是复活了?要不然这就是他的鬼魂?这一次我没感觉到他有热乎气,虽然我真希望他有啊!这件事到底是什么时候发生的?难道亮河真的已经死了?如果是这样,他也帮不了我什么忙。就算他进去,他也插不上话。他们俩能看得见鬼魂吗?我开始跟着亮河走。可他哪儿也不去,我就知道,他得回家。我跟着他进了门,换了衣服,看见他躺在鹤姐的卧室里,就那么躺着,不闭眼睛,什么都不干。他一个人把这张床都占满了。我才知道,他是在盯着对面那张画看呢。画上的维纳斯已经穿上了那件橙色的长袍,系好了腰带,那凹凸起伏的身形,比她的裸体还要诱人遐想。我从他家哭着跑出去了。门还开着,可是我没再进去。回家见到伯祖母,我冲她声泪俱下地疯狂大喊:“巷子口没有买羊杂碎的,只有豆浆!”她的话一句都不能信。我觉得,她把豆浆馆说成是羊汤馆,一定有什么伤害我的阴谋。我不会让她得逞的。 -

那丑
楼主 LV1 2016-08-18第六天二零一二年七月十七日 星期二 晴转阵雨 伯祖父傍晚出去散步,一直没回来。我们都急坏了。找了一个晚上,又报了警,我还在同城网上发了寻人启事。看门大爷也答应帮我们盯着点,但今天估计不会有消息,除非他自己摸着黑回家来。着急也没有用,只能等着。伯祖母都吓得目光发直了,说话不看人,嘴里不停地念叨说,人死了,人死了。已经几十年了,她说,从没有迷过路,不回来就肯定是死了。我只好劝她说,交警没发现附近有交通事故,伯祖一定是走丢了,他走得那么慢,很快就会被人发现的。可她不听。她把我关在卧室外面,自己去收拾伯祖的东西,说发现尸体后一起烧掉,那些“遗物”里还包括伯祖看了几十年的、摞起来一人多高的报纸和杂志。她的这些行为让我又酸楚,又无奈,还又担心,她万一真的犯了病该怎么办。好在我最后还是劝得她去睡了,答应明天早上一定告诉她好消息。为什么偏偏我来了之后出了这么一件事?我实在是忍不住要抱怨。可抱怨有什么用呢?我找不到别人帮忙了。现在我不想给我母亲打电话,我也不知道为什么,就是不想打。我相信警察能处理好。今天派出所的那个宽脸膛民警,我给他留了我的电话。有好多人都怕跟警察说话,可我一点儿也不怕。我先前觉得伯祖母是个很理智的人,可不知道她为什么对死的事情这么敏感。我都怀疑她已经疯了。我没法再计较白天发生的那些事,我心里的那些小情绪,它们跟伯祖的失踪相比,简直就是鸡毛蒜皮。不过既然是日记,还是应该都写下来的。早上我起得晚了,发现我学画用的所有东西全部失踪。我连忙检查书包的深处。幸好,鹤姐送我的炭笔还在。不管是谁(还能有谁),她要么就是没发现,要么就是害怕把我逼急了。我估计是前一种。伯祖母说,她早上看见老头拎了一包东西出去,她还以为是垃圾,就没管。可我真的没法再信了。我下楼去垃圾堆里检查了一通,没有。大概是在旁边哪个小区里吧。我来回跑了一趟,连赌气的劲头都没了。我没奈何地对她笑着说,没关系,我本来也不打算再去学画,亮河也不想再教我了。她可能是知道昨天晚上我出去过。这大概就是她表达愤怒的方式吧。听我说不再去学画,伯祖母脸上的喜悦就再也止不住了。我本来应该感动,可我的感觉却是相反的,说句不该说的,简直有点恶心。她开始围着我转,而我则想方设法离她远一些,因为她那张热气腾腾的笑脸简直就像是在讨好我。我开始瞧不起她。因为她毕竟是个大人物,我对她的敬佩是真的,可现在,这种失望也是真的。如果她每天看的不是哲学书,而是老年杂志,她今天的表现就不会让我难以接受了。我预感到今天要出事。直到下午,每个人都高兴得奇怪,连我也是。天一直很晴,直到黄昏时候,下了一场阵雨,噼里啪啦的,把人的耳朵都震聋了。伯祖就是雨后丢的。这些事好像都有那么一丝联系,但你也说不上什么来。屋里开始凉了。我从柜里翻出了冬天的被卧,心想这套东西最让人省心,在这种晒不着太阳的卧室里,有理由一年四季不换。真踏实。比它更安稳的,大概只有坟墓了。 第六夜前半夜的梦:这潭水越来越少,咕嘟嘟地冒着热气,温吞吞地沸腾了。我脚下没什么东西在盘绕着、随时准备攻击我了。它知道,我出不去。旁边还有一潭水,也像开了一样翻滚着,最后,两潭水汇到了一起。这潭新的死水向四周的岸上吐出无数张皱巴巴的丑陋的蛇皮,它们从头到尾缩成一个拳头大小,在风里摇摇晃晃,哆哆嗦嗦。一个漩涡,开始在水面上形成,越来越大,越来越深。水已经黑得像一潭墨。我发现,在我周围游着的是一条大蛇。它的腰像鲸鱼一样粗,长得没法估计,游得很慢,用它巨大的身体搅起了漩涡。它浑身冒着恶臭的黑水,溶解在潭水里,潭水才变臭、变黑的。它是这潭死水的主人。我正在被脚下的漩涡慢慢地吸进去。它的底下肯定有个黑洞,不管什么东西到了里面,都会被压得留不下一丝缝隙,哪怕是光。我还担心什么呢?反正我逃不掉。就算逃掉了,我也无处可去。我的眼睛还在淤泥里。它们早就睁开了,看见了一切,看见了我是怎么样一声不吭地沉下去的。 后半夜的梦:我手机响了。这个电话我等了很久了。“喂,爸。”“燕明啊,老头回去没有?”我没回答,因为我已经快要哭出声来了。“喂,燕明?”“嗯。没。”“记住我说的啊:出去巷子之后的那条环路,你往东走,我往西走,谁找到线索谁打电话,最后在对面会合,听见了吗?”“嗯。”“你就一个人吗?”“爸,你先到的话,一定在那儿等着我。”说完,我把电话挂了。我才发现,这条路我很熟,小的时候经常梦见它。我知道它不是环路。最东头,老是悬着一大片红日,可它更像堆上去的油画而不像真的。它底下那片海也是假的,而且说是海,却只有一个池塘那么大。最西头,有一颗很小的夕阳,它不像太阳,反倒像一个洞,正中间有个极黑的黑点。它隔着老远,吸着东边太阳的油彩,弄得那颗红日捉襟见肘,拆东补西,快要露出画布的底色了。我不管往哪边走,最后都绕不到另一边去,只能越走越远。可我只能往东走。如果我折回去,肯定赶不上他们了。我得听我爸的话,因为我们在合作,就我们两个人。天黑沉沉的,刮着狂风。清晨还是黄昏?我不知道。满街的碎纸、垃圾,都从我头顶上飞过,或者从我身边螺旋着升上天空。原来那些是……伯祖每天看的报纸,它们本来是一捆一捆地放在路边的;还有我的纸本,我画的素描、肖像……不对,我记得,伯祖母已经把它们烧了。“夜台无晓日。”这句诗谁写的来着?我真的来了。这儿是阴间。这种念头一闪过,我眼前就出现了模模糊糊的千百个影子,耳边就响起了一片含混、空洞的说话声。原来这就是我对阴间的想象啊,或者阴间就是个心想事成的地方。我安慰着自己,但心里开始越来越紧张。我知道我走不出去。不管往哪儿走,都不行。我电话又响了。“喂,燕明!人找着了,找着了。在——”没等他说完,我就把电话扔进了狂风里。老头不应该在这儿。这肯定是个梦。这果然是个梦。我猛地一睁眼,从床上坐起来了。我妈在敲我的门。“妈!妈!”我隔着门就开始大喊,“老头回去没有?”“你说什么?”我妈不耐烦地问道,“老头?哪个老头?”“我大爷爷,老头,昨天晚上走丢了,你不知道?”“什么大爷爷小爷爷的!做梦呢吧你。哎我能进来吗?”她轻轻地推开门,“你不知道你爷爷就哥儿一个吗?”我放心地吐了口气。哦,原来这一切都是梦。可书包里的炭笔呢?算了,那可能也是个梦吧。 -

那丑
楼主 LV1 2016-08-18第七天二零一二年七月十八日 星期三 阴 嘎噔噔,嘎噔噔,嘎噔噔,嘎噔噔……从潭城到农村老家,坐火车只要四五个小时,可我母亲给我买了张卧铺票。她非说我累了。现在她也在火车上,半个小时以后到潭城,去处理我留下的事情:寻找失踪的,照顾犯病的。中间的空档,我请了亮河帮我盯一阵儿。我母亲坚决不许我在老人家里再待一天,就差说那地方是凶宅了。她埋怨我为什么昨天不给她打电话。我说不上个理由,只好低头认错。就这样,我被扔上了火车。是我自己来车站上车的,当然,可我不记得一路上发生了什么,连坐的是出租还是三轮、司机是男是女都没有半点儿印象。伯祖母犯病的原因很简单,也很荒唐:早上她被阳台上的一只黑猫吵醒了,她就从地上抠起一块碎地板砖去砸它,砸中了前爪,砸得血肉模糊的,最后猫惨叫一声跑了,她也就犯了心脏病。我看得出来,这次是真的。我给她倒了好多救心丸,一着急连含在舌根下面的秘诀都忘得一干二净。不过总算救过来了。她休息的时候,我赶忙去凿亮河家的门。亮河穿着个灰色半袖,衣服裤子上抹得都是油彩,正在阳台上画画,我请他帮忙的时候,他还不放心地看了一眼颜料盘上刚调好的色彩。我当时真有心给那东西扔到窗户外头去。他来到伯祖母床边,不知道该干什么。我说照顾病人我来,让他帮着联系一下派出所,看那边找人找得怎么样了。可他一和警察通话就特别紧张,半天也没说清楚自己是谁。知道那边还没信儿后,他又大声地直接告诉我,这让我对伯祖母编一个善意谎言的计划彻底泡汤了。亮河可真是个画家。他什么时候都没忘了自己的身份,因为他除了画画,别的都做不好。可惜我这里还真没有什么画需要他帮着完成。我这儿只有一个半死不活的人,和一个半活不死的人;说错了,后面那个还不是人。它今年才十三岁。中午,我给亮河做了饭。我们俩没多说话。我说,我要走了。他问我还来吗,我说不一定。他让我留个电话,我说,我留下他的号就行了。他有点尴尬,可还是听了我的。临走时,我把伯祖母家的钥匙给他了。迈出楼道门的那一刻,我心里想,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,更不知道将来还愿不愿意回来了。命运大概不会只管手脚、不管大脑吧。我应该买个硬皮本来着。铺上太软了,左手还被手电筒占着,写的字都飘起来了。现在十点半,离到站还有一个多小时,我决定再躺一会儿。放心吧,放心吧,明天的日记肯定不一样啦:新鲜的地方,新鲜的人,新鲜的词句,最主要的,还有新鲜的水果。嗯,我会把这之前的事请全都忘干净的。燕明,加油! 第七夜火车上的浅梦:黑漆漆的墙纸。窗帘拉着。我好像又回到了伯祖母家。这地方我再熟悉不过了。可我为什么要回来呢?我在走廊里慢慢地移步。伯祖母的卧室一点一点展现在我眼前。那张深灰色的床,铺着黑色的毯子,毯子上躺着伯祖母的尸体。她死了。对了,这也许就是我回来的原因。只有我才有钥匙。我去请亮河来帮忙。他慌慌张张地跑出来,问我要干什么。我说,请他给伯祖母画一张遗像。他一脸悲哀地说,他非常乐意帮这个忙。亮河在伯祖母旁边支起画板,正要用铅笔画轮廓,她的尸体就迅速腐烂,好像被点了一把火似的那样起皱、塌陷,变成一具狰狞的干尸。她用这种办法拒绝被画到纸上、裱进相框里。同时,她开始絮絮叨叨地说起话来,可听不清说的是什么。亮河告诉我,她是在乞求我们不要忘记她。我想不到让她闭嘴的办法,因为她的嘴唇和舌头早就烂净了,牙齿裸露在空气里,可那声音是没有消逝。这时候,鹤姐走了进来。她一身鲜艳的橙红色,手里拿着鞭子,气愤地朝尸体狠狠地抽打下去,直抽得它皮肉碎裂,骨头飞溅,不再发出任何声响。 -
-

-

-

-
-
-

-
-
-

-

-

-

-
-

-
-

-
-

-

-

-

-
-

热门参赛作品
- 1
-
2
无域之境
其子狡娈
···吾名殷封,是这无域之境的主人··· ···若想要这里的宝物,就来交换吧··· ···留下你的姓名,留下你的交换品··· ···记忆,情感,时光,或任何东西··· ···当然,你也能拿自己的宝物交换··· ···至于换到什么··· ···一切皆是缘··· ··· ··· ··· ··· ··· ···
-
3
读书之旅
断断
《兔子什么都知道》 这本书是发生在时光森林里的故事。这片以胡萝卜为名的森林里住着许多只长着温柔的红眼睛的兔子。其中有深爱着彼此的兔小灰和兔小白,有互为冷暖的兔小冷和兔小暖,有忧伤的总是睡不着觉的兔小眠,有疯癫地每天想着逃离这个世界的兔小枫,有整天念叨着说要减肥但仍然舍不得抛弃胡萝卜的兔小胖。一只兔子所喜欢的:胡萝卜和白菜;小草静静生长的声音;一朵花努力展开自己时的姿态;从枝叶的缝隙间照进森林里的光,七月午后一阵突然袭来的凉风;轻轻落在小溪水面上的雨滴;冬天里的第一场雪;印在雪地上的两排小脚印;以及,另一只兔子的体温。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只柔软的有爱的兔子,一起找到心底的那只兔子吧~ 德国哲学家康德说过:“这个世界上唯有两样东西能让我们的心灵感到深深的震撼: 一是我们头上灿烂的星空,一是我们内心崇高的道德法则。” 读书,让我们不孤单,可以看到银河里那些古远,孤独的星星。 他们是夜空里最亮的星。 从小时候开始来说吧, 《伊索寓言》,《格林童话》,《安徒生童话》 小学的时候,就喜欢上了读书,可是那时候没有自己喜欢的可以读,其实说实话是没有书可读。 一本作文书我都可以津津有味地读好久。 进入初中,租书,买书更多了,影响较大的有: 《活着》,《许三观卖血记》,《十八岁第一次出门远行》《荒村公寓》,《狼图腾》,《废都》 贾平凹的狂放之风,余华的悲观但努力的气质。 《小王子》则是读过的次数最多,星星盈盈,童心未泯。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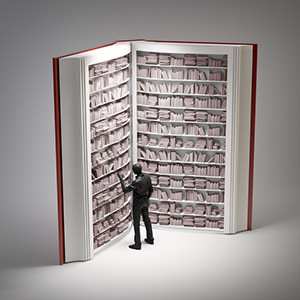
 2094
2094
 举报
举报
 收藏
收藏
 分享
分享
 回复
回复
 新浪微博
新浪微博 QQ好友
QQ好友 QQ空间
QQ空间
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30452
京公网安备11010502030452